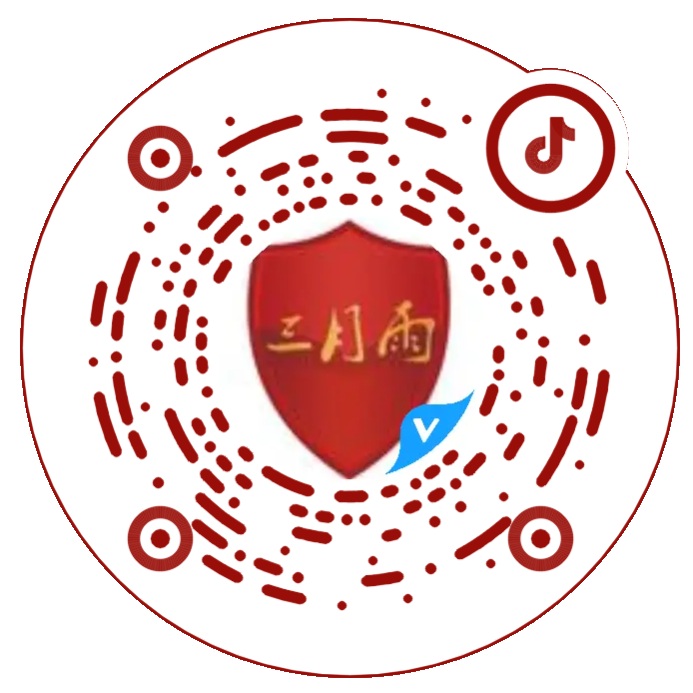严以治官,宽以养民

我国具有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,其中法律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传统法是先贤为治理国家服务的举措之一,治理国家有其“道”,故传统法必有一以贯之的“宗旨”。那么,“宗旨”到底为何?
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先生苦心孤诣,撰写大量论著,力图阐述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文化火种。先生晚年,思想达于炉火纯青之境,写出了《读通鉴论》和《宋论》这两部史学评论经典。他的史论,并不单纯就史论史,更是要借史论道、明道。在《读通鉴论》中,他概括出“严以治吏,宽以养民”一语,将中国法制宗旨一语道破。在这里,吏指的就是官。所以,这宗旨实际上便是“严以治官,宽以养民”。
传统法为何“严以治官”
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主要是由先秦儒、法两家所型塑,二者区别何在?按照中国政治思想史大家萧公权先生的归纳——儒家重民,法家尊君。在春秋战国时代,重民的儒家被当政的诸侯国君视为迂腐而不切于实用。到战国中晚期,法家逐渐得势。法家人物基本上以国君谋士、策士身份来著书立说,目的是给时君世主设计出一套足以“立功”的办法,即以法、术、势三者相结合,驱使臣民尽力于耕战,从而国富兵强,无敌于天下。其中,韩非子献策建言:“人主者,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。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,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,故明主治吏不治民。”这就是传统法“严以治官”的思想来源。
在封邦建国、贵族世袭的西周和春秋时代,依靠血统解决了国家治理权问题。因为那是一个“血而优则仕”的时代,贵族永远是贵族,不管你是不是贤能、贤才。但是,进入战国以后,井田废、阡陌开,土地私有,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贪欲;与之而来的争战,使各诸侯国君经常处于亡国丧身的危机之中,以血缘“封土而治”“分地而食”的分封制由此走到了历史尽头,中央集权、广设郡县的体制应运而生。在国家权力集中于国君后,面对地域辽阔、郡县众多的天下,国君靠一己之力无法治理。于是,接受国君的委任而去管理天下的郡守、县令等官僚,最终取代血缘贵族。
尽管韩非子提出了治官的思想命题,但他过于侧重用术,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设计。当然,建立一个完整的依法治官的制度体系,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经验累积。汉初统治者吸取秦始皇的教训,推崇无为而治,慢慢积累经验,终于在武帝时把运作中央集权制大帝国的“软件”大体设计出来。这个“软件”就是外儒内法。韩非的“明主治官”思想经过七八百年的摸索,逐步制度化、规范化,到唐代才算基本成熟。
尽管自秦用法家二世而亡,法家也落得个刻薄寡恩的恶名,却又因其的确符合国君的要求且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仍备受关注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晋元帝司马睿即将《韩非子》一书赐给太子,也就是后来的晋明帝司马绍。《宋史·孙永传》提到,宋神宗赵顼为颍王时,将自己新抄录的《韩非子》交给僚属校订,孙永指出该书不合儒家经义,不应如此上心,赵顼委婉回答:“广藏书之数耳,非所好也。”这些史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帝制中国,法乃是帝王“严以治官”的重要工具。
传统法如何“严以治官”
纵览传统法史,自汉以来“严以治官”主要是通过对加强立法和司法来实施的。
在立法上,历代法典设置了相当多的关于治理官员的条款,其内容涵盖官位的设置、官员的培养和教育、官员的选拔、官员的职责、违背职责的处分和官员的监察等方方面面。以《唐律》为例,总计502条,直接规定治官的达274条,占总数54.6%;其他的条文,除了一些纯技术或程式方面外,其他的规范对象多是“民”,或者是包括“官”在内的所有民众。即便是这些重在规范“民”的条文,也需要“官”的作为才有实现的可能。宋、明、清三朝律典皆本《唐律》,到清代,除《大清律例》之外,还有大量的则例、会典、单行法规、地方法规等。这些卷帙浩繁的成文规条,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强化对各级官员的管理。故而,“严以治官”一直是传统中国立法的首要关切所在。
在司法方面,除了轻微的自理案件之外,历代都要求各级官员断案在“法有正条”的情况下进行;“断罪”需严格“引律令”,若遇疑难案件而无成文法条可引时,则需遵守轻重相举或比附相近的条文来拟出断案意见,供上司衙门采择,否则即要承担“出入人罪”之处罚。到明清时期,比附援引是否有效,还须由皇帝来最终决定。
以“宽以养民”证成“严以治官”的正当性
韩非的“严以治官”说,以实效见长,故在帝制时期,被多数统治者奉为圭臬;其短则是流于极端功利,将民众完全视为被治理对象,故注定它最多能收效于一时,而非长久之计。
秦汉统一后,随着治理经验的累积,终于确立了以外儒内法为核心思想依据的治道。早在西周,就出现了“民本思想”。所谓“天聪明,自我民聪明。天明畏,自我民明威。”因儒家重民,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,也必须关注百姓之利益,倾听百姓之呼声。传统法“严以治官”,不是为“治官”而“治官”,也不是单纯为了统治者的“家天下”而“治官”,而是为了天下百姓而“治官”。“治官”至此才有了充分的理由。到明末清初,王夫之精研历代治道和治术,概括出“严以治吏,宽以养民”一语,将法家的“治官”说内化到儒家的“养民”说中,赋予了“治官”说崇高的目标和价值追求。
“宽以养民”,是指统治者和各级官员要将“民”视为“养”而非“治”的对象;而且不是一般的“养”,乃是“养”之以“宽”。“宽以养民”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亦有很突出的体现。其著者,如在立法上,以均田均赋役为主要内容的打击地方豪强之举措;逐步废除酷刑,改变重刑倾向,彰显罪刑相适应原则;将儒家伦理纲常逐步法制化。在司法上,倡导对细故案件的灵活审理,注重家族乡党内部的调解息讼等。
传统中国儒家既重“经”(原则性),更重“权”(灵活性),主张在实际中必须经权结合。《四书》之最深奥者《中庸》,主要是讲君子如何“时中”,即如何拿捏分寸以固守大本达道。王夫之提示我们:“严以治吏,宽以养民”是“经”,在具体施行中更要讲“权”,拿捏好治官与养民之间的分寸,即治官服务于养民,治官本身不是目的。
以“严以治官,宽以养民”为宗旨的传统法,在其数量浩瀚的条文背后实有历代先贤的苦心孤诣和法律实践经验,即便时至今日,其价值仍旧不可磨灭。
来源:李启成
(声明:“三月雨”微信公众号刊载此文,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。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及时与我们联系,我们将及时更正,删除或依法处理。)
浏览量: